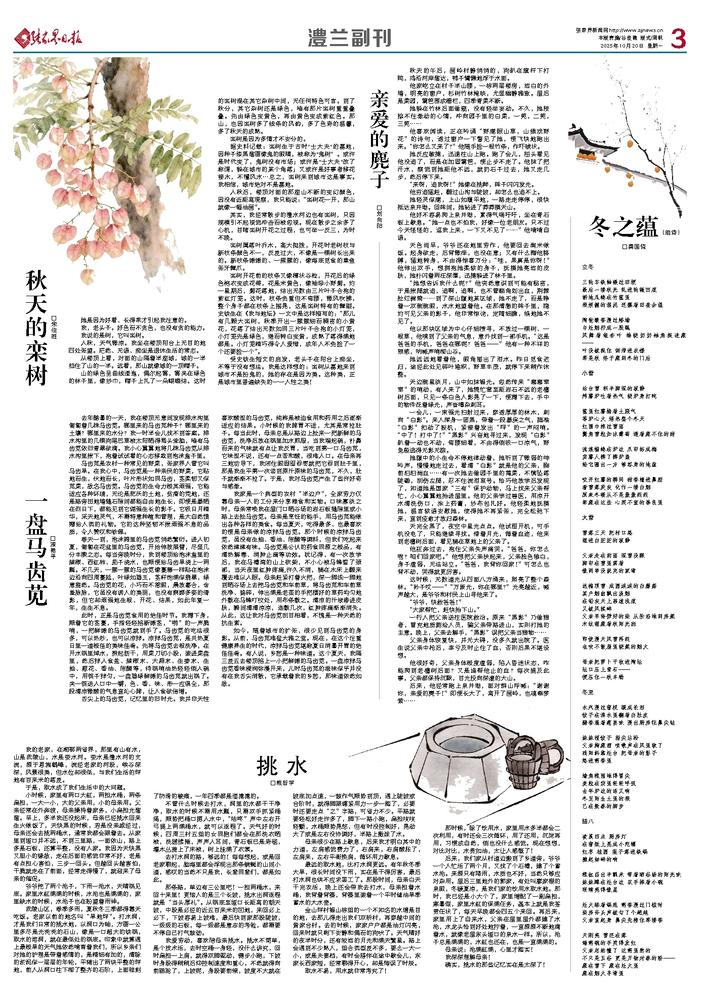□熊哲学
我的老家,在湘鄂两省界,那里有山有水,山是武陵山,水是娄水河。娄水是澧水河的支流,源于恩施鹤峰,流经老家的河段,峡谷深深,风景很美,但水位却很低,与我们生活的坪地有百来米的落差。
于是,取水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大问题。
小时候,家里有两口大缸,两担水桶,两条扁担,一大一小,大的父亲用,小的母亲用。父亲经常在外奔波,母亲操持着家务,小扁担光溜溜。早上,多半我还没起床,母亲已经挑水回来生火做饭了,天快黑的时候,若是没亲戚经过,母亲还会去挑两桶水,通常我都会跟着去。从家里到垭口并不远,不到三里路,一面依山,路上多是石板,还算平整,没有人家。我因为天快黑又胆小的缘故,走在后面的感觉非常不好,老是有点担心害怕,三步一回头。但越回头越害怕,干脆就走在了前面,经常走得慢了,就迎来了母亲的催促。
爷爷挖了两个池子,下雨一池水,天晴锅见底。家里水缸满满的时候,水池也是满满的,家里缺水的时候,水池子也在盼望着雨神。
武陵山区,春季多雨,夏秋冬三季都得靠天吃饭。老家以前的地名叫“旱地坪”。打水洞,才是我们日常的挑水地,以洞口为轴,方圆一公里多尽是光秃秃的石山,像是一口超大的铁锅,取水的溶洞,就在最低处的锅底。印象中就算遇上最极旱的天气她依然哺育着我们,所以乡亲们对她的护理是带着感情的,是精细有加的,清除的淤泥似一层层的年轮,平辅出了两块平整的坪地,前人从洞口往下彻了整齐的石阶,上面锉刻了防滑的棱痕,一年四季都是湿漉漉的。
不管什么时候去打水,洞里的水都干干净净,取水的时候不需用水瓢,只需双手抓紧桶绳,顺势把桶口摁入水中,“咕咚”声中左右开弓提上两满桶水,就可以返程了。天气好的时候,四周三村五组的女同胞们都会在那洗衣晒被,洗搓揉捶,声声入耳间,青石板已是彩毯,灌木丛盖上了床被,树上挂满了衣裳。
去打水洞的路,够远的!每每想起,或是回老家聊起,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那条蜿蜒的山间小道,感叹的当然不只是我,长辈同辈们,都是如此。
那条路,单边有三公里吧!一担两桶水,来回十来里!更恼人的是三个长坡,挑水出洞返程就是“当头厚礼”。从锅底至垭口长距离的朝天坡,中段是必经的近五百来米的凹地,来回必上必下,下坡容易上坡难,最后快到家那段陡坡,一级级的石板,每一级都是意志的考验,都需要不停自己打气鼓劲。
我爱劳动,喜欢陪母亲挑水。挑水不简单,是个技术活,去时空桶一身轻,没什么讲究,回时扁担一上肩,就得双脚驱动,健步小跑,下坡时身段得稍稍后仰控制速度和重心,不然就得向前踉跄了,上坡呢,身段要前倾,坡度不大就在坡底加点速,一鼓作气顺势到顶,遇上陡坡或台阶时,就得脚跟绷紧用力一步一踏了,必要时还要走点“之”字路,可省力不少。平路就要轻松好走许多了,脚下一路小跑,扁担吱吱轻颤,水桶顺势晃悠,但有时没控制好,晃动大了或是左右没协调好,半路上撒泼了水。
母亲很少在路上歇息,后来我才明白其中的力道,左肩感觉费力了,右肩来,右肩酸胀了,左肩来,左右平衡换肩,循环用力歇息。
最远的取水地,比打水洞更远。有年秋冬季大旱,很长时间没下雨,实在是干得厉害,最后打水洞也供不应求罢工了。那段时间,母亲白天干完农活,晚上还会带我去打水,母亲担着水桶,我背着背篓,背篓里装着一个平时储油旱季蓄水的大水壶。
金山坪村银山栋组的一个不知名的水塘是目的地,去那儿得走出我们双桥村,再穿越中间的黄家台村。去的时候,家家户户都是油灯闪亮,回来时就只剩下安静和偶而的狗吠了。天气晴好的夜半时分,还有皎洁的月光和满天繁星。路上会遇到不少熟人,组合类型差不多,要么一大一小,或是夫妻档,有时会搭伴在途中歇会儿,东家长西家短,经常聊得开心,却是悔误了时辰。
取水不易,用水就非常考究了!
那时候,除了饮用水,家里用水多半都会二次利用,有时还会三次循环,用了还用,沉淀再用,习惯成自然,倒也没什么感觉。现在想想,对比对比,水贵如油,太让人感慨了!
后来,我们家从村道边搬到了乡道旁,爷爷一个人忙活了两个月,又找了个石槽,建了个蓄水池。来源只有降雨,水质也不好,当然只够应对杂用。屋后三里地外的郭家,有处叫廖家棚的泉眼,冬暖夏凉,是我们家的饮用水取水地。那时,我已经是小大个了,家里增配了一副扁担,寒暑假,家里水缸的保满任务,基本上就是我签责任状了,每天早晚都会四五个来回。再后来,家里用上了自来水,父亲在屋里屋外都建了水池,水龙头恰到好处地拧着,一直源源不断地滴着水,就像老屋东头垭口的泉水一样。所以,池子总是满满的,水缸也还在,也是一直满满的。
母亲说:池满缸满,心里才踏实!
我深深理解母亲!
确实,挑水的那些记忆实在是太深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