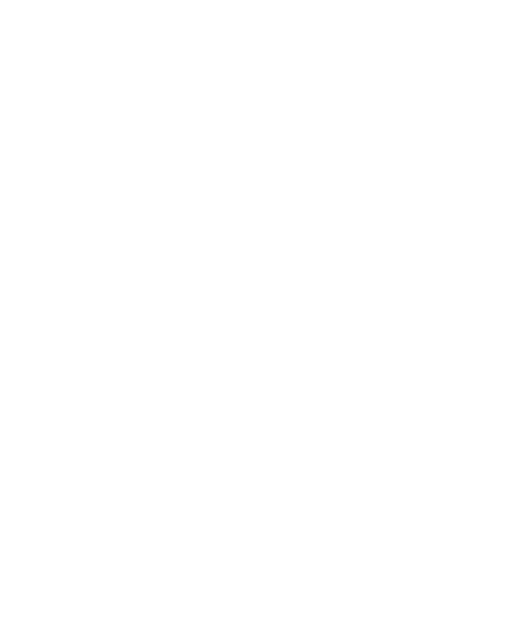宋梅花
从老南门口搬迁来到新安置区,已有5年,幸好,还是在河边,且隔古城不远,下楼,过马路,是正在修建的古城。这成了我总爱下楼去河堤走走的理由。
古城还没完工,临街很长的围墙,让人只能看到那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翘檐梁壁。横过马路,是古城临时停车场,大门里全是土路,铺了些沙砾,便于停车,大片的空旷地带,散堆着很多建筑材料,靠河的围墙,隔断了我的视线,河对面的高楼大厦纷纷从墙头跳进半截跃入我的眼帘。围墙像长长的铁箍,提示着人们,这里是未竣工的古城。
走进临时停车坪,看到一些绿,一些黄,一些枯草。很喜欢靠近闹市有这么自然,没有人工修饰的地方。大门左边,便听见水声,望见一条溪涧,准确地说,是一个下水道流水汇聚的地方,几股水汇在一起,发出脆脆的叮咚声。堆积的杂土间,早已长满各种杂草和藤蔓,甚至还开有一两朵秋南瓜花,绿绿的藤蔓伸展着那两朵花,充满生气。突然一只白鹭扑搧着翅膀从草下飞出来,几秒钟便飞远了,快得让我无法快速拿出手机拍它的翔姿,是和它出去找早食起飞的巧合?还是我的脚步声惊吓了它的晨梦?总之,它飞走了,飞走的那一刹那,翩跹着洁白翅膀的模样很柔美。
无法留住白鹭,我便仔细亲近脚下的秋草,秋草中夹着很多无序的狗尾巴草,开着好几种叫不出名的花,草叶花瓣上的露水,晶莹无声地望着我,文静地微笑。俯下身子,我的眼睛在花瓣上那层薄雾间游移,那是秋露吧。秋露,在古城的边缘。古城,在一墙之隔的河边,虽然,它已不是我曾经的南门口,但依然喜欢。秋露给人梦幻般的暇想,古城则在晨曦中显得有些神秘。
我的眼睛好不容易从秋露的朦胧中抽回,一转头,一树鹅黄跳入眼帘。那是什么花?一条一条伸展的绿枝上,挤满了许多鹅黄色的小花,近看,是很多的小朵,有规律地挤在一起,隔远望去,便成大朵大朵鹅黄,在大片飞絮中格外显眼。这几瓣鹅黄,让我凝目,驻足,徘徊,在那片秋絮。我不知道这里的草有多长时间没打理,或是根本没打理过?成片的草絮,挂着无数半透明的絮球,一碰即落。它们是种子吧?风一吹,不知哪块地又是一大片飞絮?自然界的生命力是无尽的,随时随地,都可看到花的盛开,绿意的展现。如这树鹅黄,这片秋絮……
靠河的围墙边,堆满了高高的木板,许是很久不曾用到这上面来?或是在修建时这些模板早已派上过用场?它们已经全被绿色的藤蔓植物覆盖,植物的力量是巨大而无声的,当你感觉到它时,已是牵藤遍地满眼绿。那些细细长长挂着叶片的藤条,和那些木块配衬,竟带着一种古朴的气息,着实好看。我想,这些藤蔓,肯定是肯定爱热闹的,它们从河岸爬上围墙,再长满这些堆砌物,和我一样,随时关注着古城的修建。
停车坪的左边,是一个大斜土坡,坡底,可看到古城高高的墙基脚。一个废旧的小推土机放在坡边,铁板和轮胎处开满白色的苍耳花,有些素雅,很是具有艺术感,几朵花在轮胎和铁板前对我浅浅笑着,让我想起两个字:素秋。如果要我以它们为题写诗,我就用素秋为题。只是,我不是写诗之人,写不出素秋的静美。
往坡下走,沿路开着成片的黄色小花,这遍地的秋黄,竟让我搞混淆了,是野山菊吗?不像。哦,想起来了,它叫千里光,名字干脆响亮,不拖泥带水,想来,应是花如其名?听人说“有疮无疮,只怕千里光。”这千里光,是药材呢。我想着去找它们说说话,去摸摸那些黄黄小小的花瓣,却发现小飞蝇和蜜蜂比我早。一只小飞蝇落在花瓣上,它是睡着了?还是被花香沉醉了?动也不动一下,那么,是露水打湿了它的翅膀?还是在做一个关于秋虫对露水呢喃的梦?蜜蜂仍然很勤劳,不管什么花,都少不了它的身影,几只蜜蜂,早已悄悄在花间穿梭飞舞,相比之下,小飞蝇是多么懒惰。
隔着那些草花,能看到古城上面有人不停吆喝着走来走去,那是工人师傅在干活,快修好了吧?我已看见那一排排的翘檐和翘檐下的门面,以及长而平整的青石板路。一辆很长的工程车正从门口“吱吱嘎嘎”叫着开进来,吃力地喘着粗气,车上严严实实地堆放着很多铁板和铁柱钢筋,这一大车材料,不知要花多少钱呢,满满的一大车,想来这古城的建筑都是这样一大车一大车拖来的材料砌成的?真不容易。聚沙成塔这句话真是没说错的,这么大的古城,已修了好几年,就是这么一点一点,渐渐显出了轮廓,或许,它会成为下一代甚至很多代人心中的南门口,继续着庸城故事,绵延下去。
南门口安置小区和古城相隔不过百米,是我欢喜的。古城在,老南门口就在,并没有因为搬迁,南门口就渐行渐远。相反,时代的变迁,让老南门口的人住上了电梯房,经过装修、搬家的折腾,安定下来的老街坊们又聚拢来,没有了老南门口的街檐,却有了摆放在电梯外通道口的小椅子小桌子。小桌子用来打小牌,打扑克,小椅子用来坐,全是老太太老公公。每次从过道上楼,我总是在人多的地方慢下脚步,那些布满沧桑和皱纹的脸,个个神态安然闲适。由原来的河街、南门口、桥湾搬到这一栋栋电梯楼,对他们来说,是翻天覆地的变化,欣喜并适应着依然处在闹市中的新家。
记得去年夏天,楼道的走廊两边坐满了乘凉的人,我经过时,一位大婶使劲对我望,然后叫我的名字,我回头一看,原来是曾经的邻居,住在老巷时,一个四方的小天井,隔着我家和她家,早相见晚相见。她老了,可是模样没怎么变,她问我:“你妈还好吧?”我笑笑:“挺好的!您还好吧?好久未见……”见我回话,她有些高兴,忙不迭地告诉我,她家住在6楼,她儿子住在7楼,我一听:“没隔多远呢,还是一栋楼哩!”她高兴地说:“那好啊好啊!”想想曾经屋挨屋住着的邻居,现在也是楼上楼下地住着,并没有走远,我感觉一种莫名的安慰。远亲不如近邻,虽然生活中有过磕磕碰碰,能在一起成为邻居,也是一种难得的缘份吧。
想起那年,母亲站在刚从老屋搬出来的最后一点物什旁边,眼睛盯着老屋旁的挖机,三下五除二就把她辛辛苦苦返修的老屋移为一堆瓦砾,心里很是不舍,毕竟住了那么那么久啊。就在那时,隔壁巷子的田婶走到母亲面前说了句:“谷老师,这一搬,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呢。”说完,两人便傻傻对望着,又傻傻一齐转过头望着那些堆破瓦乱砾发愣、沉默,田婶曾和我家因为一些小事闹过矛盾,多年不讲话,却在这将要离开老街的那天,主动和母亲说说话,想来心里那种怨气早消了。
现在看来,都还住在这几栋安置区楼里,没有走远。原来在老南门口的恩恩怨怨、磨磨擦擦,都已烟消云散,剩下的,只有相见一笑泯恩仇,再添加一种淡淡的挂念。很多的过往,都被浓缩在一起。很多的南门口故事,街坊情,南门口情,都被浓缩在这里。岁月并没有走远,只是换了一种方式,如此,甚好。
(作者系市金海实验学校小学部教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