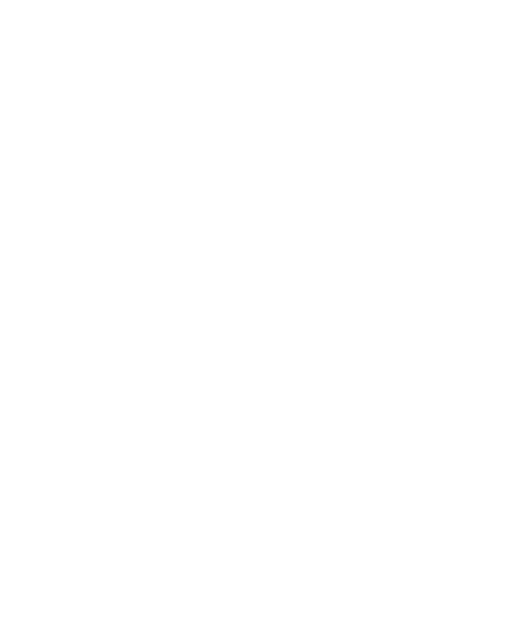□方辉
套用一下乡土文学之父沈从文先生的叙事风格:“我随过无数次的份子钱,喝过许多品种的酒,吃过各种场合的席,却唯独只怀念儿时吃过的大席。”
现在想来,那个时候的大席之所以好吃,原因不外乎三个字:“原生态”。说来也怪,一切就像是上天安排好了似的,每个村寨总会有那么一到两位精明能干且声音洪亮的长者, 但凡红白喜事,他们都是当仁不让的操盘人,乡人敬称为“督管”。督管会用墨笔把帮工诸人的职责在红纸上列写得清清楚楚,然后贴在堂屋或者厨房门框的醒目处。那唱了大半辈子山歌的嗓子这时候便平添了几分不怒自威的霸气,被派到工的不论是何种样脾气的人,这个时候一律会驯服地领了命,麻溜地忙活去了。
于是乎画面逐渐清晰起来:土灶的灶门边堆积着小山似的柏木劈柴,负责向火的人不时地左右开弓,向膛内扔几块劈柴进去。那些干劈柴的纹理丝丝可见,像是上好火腿酱红色的肉丝,在火膛里发出令人愉悦的香味。红蓝相间的火苗疯狂地舔舐着锅底,厨房里热雾蒸腾,到处弥漫着甑子饭和菜肴诱人的香味。土灶的两口大铁锅,一口用来蒸甑子饭,一口用来炒菜。大铁锅炒的菜一般是可口的时令菜蔬,需大火猛炒,以保证鲜脆爽口。而肉菜,一般会盛放在靠厨房墙边的那一排煨钵里,煨钵周围是一圈从火膛里撮出来的暗红色的炙热火炭子。文火慢煨下,这些土猪土禽的肉香味与嫩花椒,老桔叶等香料的香味水乳交融,变得酥烂鲜香,汁浓味美。湘西流行吃流水席,有煨钵在,后面来的人,即使在隆冬时节,也能保证吃得上热呼呼儿的饭菜。
上面讲到了大席的“原生态”属性:禽畜都是用粮食自养的,米和菜是自己种的,油是自己榨的,柴是自己砍的,炒菜的厨子也是本村的乡邻。甚至那些煨钵,那些上菜的托盘,那些摆席的高脚四方桌,都是邻居们自发从家里拿来的。办酒席当然少不了酒,那些酒可是从“猪场”那边打来的地道粮食酒,一般为米酒、苞谷烧,再不济也是地瓜烧。之所以说到“猪场”,是因为酿酒剩下的酒糟,被就地拿来养猪了。成年后我喝过很多所谓好酒、名酒,却始终难以忘记“猪场酒”的味道。
湘西大席好吃的另外一个要素是“氛围”。几张、十几张大桌摆满了吊脚楼前的坪塔,菜品丰盛,热气腾腾,不够管加。人们大碗喝酒,大块吃肉,白狗黄狗们卧在桌下,用爪子捧定了骨头大嚼,肥猫撅了尾巴在食客们的裤腿上摩来蹭去撒娇。这喧闹人声伴着鞭炮和锣鼓声在山坳里久久回荡。间或听到督管扯长了嗓音唱喏道“帮忙滴接担子……”,人们便不约而同地停了箸顺声望过去——来者大抵是主人家的上亲。挑夫的箩筐里堆满了谷米或者礼品,把扁担弯成了满弓状。那挑夫配合着有节奏的”嗞嘎嗞嘎”声,在窄窄的田埂上健步如飞,精瘦的小腿上肌肉块块饱绽……
响手们鼓起腮帮,吹奏出欢快的曲调,猛然把气氛推向高潮。那个时候民风淳朴,去吃席不一定非得拿钱,用立背篓装上一满篓干谷子就好。倘若能用箩筐挑上一满担谷子,就算得上是很上台面的礼行了。主家也格外殷情好客,大碗大盆地上肉上菜,倾其所有。乡间的席,一般至少是要管两餐饭的。那时候交通不畅,远来的客,都是要留宿的。不待主人家吩咐,热情的邻人们便会自发地将他们领回家去,给安排上最好的床铺……
太阳偏西时分,席也吃得差不多了,喝得醺醺的酒客们打着嗝,横披了衣裳,三三两两地勾搭着肩膀,蹒跚地消失在夕阳古铜色的余晕里。
邻居们这时会自发地过来帮忙捡场,人们无声地、麻利地忙活着。主人家会将借来的盆和钵里装满肉、菜,一一送还,邻居们推辞一番,开心地收下了——接下来好几餐都不用炒菜了!
祖母是1996年冬天去世的,最后的日子里,我母亲问她还想吃点什么,祖母用手指了指锣鼓声传来的方向——有本家在风光嫁女。听说祖母想吃大席菜,主人家大方地送来一大盆热腾腾的甑子饭,一大陶钵香喷喷的熬肉。其实,祖母早已吃不下任何东西,母亲把食物端到她面前,她只用干枯的手扇了点烟子闻了闻,缓缓说道:“好香哟!”母亲要喂给她,她摆手制止了,然后艰难地挤出一丝笑容,对我母亲说道:“把你干恼火哒,这些大席菜,你稍微补下身子……”母亲背过头去,泪如雨下。
自祖母去世后,日子似乎突然变快了,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,农村大席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,徒留一幕幕回忆。
作为资深旅游人,许多餐饮界大佬向我咨询怎样去挖掘、寻找到本土的饮食特色,我想都没想,脱口而出——“大席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