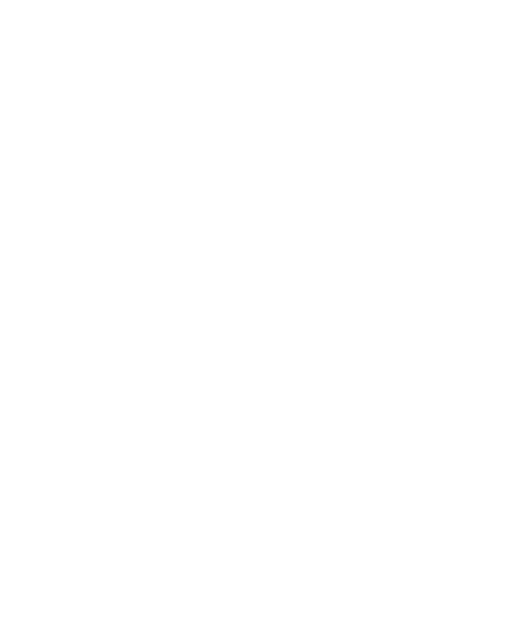□袁姣素
刘克邦的散文集《涟水谣》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,分为“流年缱绻”“旖旎山水”“心灵亮光”“记忆犹新”“人生品味”“读有所感”六小辑。无论是品味人生,还是纵情山水,抑或驻足流连,都有文如其人的温润与暖色。先生虽曾履任公职,却格外钟情于缪斯女神,那份景仰与敬畏在字里行间缱绻,动情,延伸。岁月经年,恒河沙数,刘克邦用生活的珍珠穿针引线,笔耕不辍,著有五部散文集,他的散文作品大抵是他亲历的人事风物,大可见雅,小怡生情,新著《涟水谣》与他之前的几部文集相较,特色鲜明,更具有其个性话语。
刘克邦的个性就体现在“人文统一”的标准上,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秉性,为人刚直不阿,喜欢济人危难,且真挚为文,真诚待人。
“文如其人,人如其文”,一直是散文形式中的“真”之体现、文化道统,亦是人们呼吁的散文艺术的精髓。众所周知,自现代散文的“个性文学”观确立之后,散文最直观的“为人生的文学”就慢慢演绎成了“我口说我心,我心抒我情”的自由无拘的状态,散文的“真、气、神”也随之成为人们追崇的风向标。
《涟水谣》在其个性话语的酝酿中,有着见情见性,去伪存真,朴拙天成的况味。读来亲切可感,趣味盎然。如一杯酽茶,闻之清淡,品有余香。茶余饭后,沉湎其中,自觉一股真气行走肺腑,给人向上、向善、向美的力量。“流年缱绻”中的《贵人》一文讲述的刘老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背景下,冒着风险跨越红线,帮助作者报名读书。作者不负厚望,一举中第,开启了全新的人生旅程,成为一名造福社会的公职人员。因了刘老师的心有慈悲,给社会输送了栋梁之才,也成为了作者感念不已的贵人。
人生在世,总有危难之事,《邻居刘四爹》《张科长》中讲述的真人真事亦可见一斑。在“真情”叙事的摹写中,刘克邦对情感释放的把握力度也是拿捏自如,散文中的真气生发与其生活细节和心理描摹有着血肉相连的默契,譬如《邻居刘四爹》中的那段艰苦的岁月,大人碍于脸面总要小孩去别人家借米,作者的父母也不例外。而这个任务不仅仅是对作者脸面的一次考验,更是让他直面灵魂的拷打。因为作者在刘四爹的地里偷挖了凉薯,并当场被他发现。而刘四爹并没有揭发他的“罪行”,也没有向他的父母告状,作者从侥幸心理过渡到害怕,到内疚,再到去刘四爹家里借米,而刘四爹在自己家都面临挨饿的状态下,毫不犹豫地把存余不多的粮食借给了他。刘四爹包容、宽恕、理解的暖心一刻让作者的情感闸门一泻千里。
虽是老派的传统叙事,却可见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所蕴藏的巨大能量,在解剖自我的同时能够抵达救赎灵魂,升华高度的意境。而从另一视角检阅人情世故,可见出作者在坎坷命运中所遭遇的侠义心肠,金秋之暖,其恻隐之心,体恤之爱,动人心扉,刻骨难忘。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的感谢、感恩,无不让人动容与深刻。所谓赠人玫瑰,手留余香。也许,正是曾受恩于人,或是这种生活的磨难锻造了刘克邦的古道热肠、关注弱者、助人为乐的精神,同时也练就了他人文统一的品格。大千世界,芸芸众生,世态炎凉,无论是雪中送炭,还是锦上添花,都能让人永镂于心。但雪中送炭的情怀更上层楼,更能触动人的灵魂,引发共鸣,使人心心念念,不敢相忘。所谓“文学即人学”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正是用文学的力量来体现这人世间的爱恨情仇。
从散文的文学特征看,无论是思想性,还是形象表现,都与语言艺术的抒发有着密不可分的内里联系。这种理性的逻辑思维,辅以感性的情感脉冲,能够准确地反映变动的事物,有着平地起惊雷,和以小见大的力量。譬如“流年缱绻”中的《涟水谣》在其个性话语之外,懂得艺术加工,舒缓有致,画龙点睛,佐以情感细节传神动人,更有着另一种寻常生活中的震撼。文中所讲述的她和他的故事具有历史的纵深感,在时代的洪流中,刘克邦用真实感人的故事塑造了两代人的生命轮回与爱恨情愁。在风云变幻中,“他”与两个女人的恩怨情爱,命运多舛,凄楚彷徨,展现的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与苦难。当教书的母亲病重在讲台上倒下,最终因种种因素也永远离开了人世。当那个当年被父亲轻视和伤害的“她”把这个年幼的孤儿揽到自己的胸前,此刻的灵肉碰撞有一种“此处无声胜有声”的缠绵与矛盾纠葛。让人体味人生苦难,千折百回,感人肺腑。
这种人间烟火味的人性抒写不仅仅是深情回望,烙下时代洪流的印记,其大爱情怀,悲天悯人之力,直抵灵魂,更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品格。诚然,散文之美贵在语言,美在意境,《涟水谣》的笔力之工,匠心独运,晓畅自然,蕴含深刻,有一种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心灵回归和安宁:“他们是我的亲人,与我血脉相连。我不说出他们的名字,因为,他们又不仅仅是我的亲人,他们更是在命运河流中泅渡的每个人的亲人——他们是人间灯火中最孤独、最寂寥,又最寻常、最温暖的那一屋灯。”
而在《书店里的合影》中,几个青春靓丽的姑娘在书店要求与作者合影,虽素昧平生,却因人之本性,爱美之心,受追捧的荣耀心理,便欣然应允,最后待她们离开后,又懊悔不已。“与姑娘们合影时,‘冠冕堂皇’,一本正经,怕丢面子,怕失身份,硬充汉子,没有向她们要个电话号码什么的,以便以后有个联系。”寥寥几言,足见作者的性情与耿直。
秦牧说,散文作者在作品里面,不但应该以具有个性的语言适当发挥议论,还应该直抒感情“倾诉胸臆”,这才能“以情移人”,使读者读来感到亲切。如果一个散文作者不敢流露自己的感情,不敢用自己的个性语言讲话,这样的散文,艺术感染力就会降低,因为那作为文学作品的特征被消弱了。刘克邦先生就敢于以自我的“个性”话语提炼生活,剖白自我,抒发感情。他的语言朴实接地,简约有力,个性鲜明,不求唯美,有自然而然的味道。
刘克邦不仅人文底蕴丰厚,他的游历也很丰富,《涟水谣》中《千年南丰》《浔龙河的故事》《明月照吾乡》等篇什所见所感,特色各异,饶有趣味,以在场的视角议论抒情,挖掘当地人文历史,纵深高度,给人以亲临其境之感。虽是流连山水间,迷醉风景处,却情景交融,笔墨生情。如涓涓细流,款脉脉深情,感喟生发真实自然,予人深思和回味:“这一路上,我听见千载而下的风雨如晦、阳光如禅,听见鸟雀们在岁月里叽叽喳喳,叩问着此生何寄,用它们丰满的羽翼书写这方山水隐秘的文化密码。”
古人云,大直若屈,大巧若拙,大辩若讷。刘克邦的为人为文,直抒胸臆,不藏拙弄巧,不惮于剖白自我,坦荡磊落,从善如流,有容,有心,有情,有一如既往的真我风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