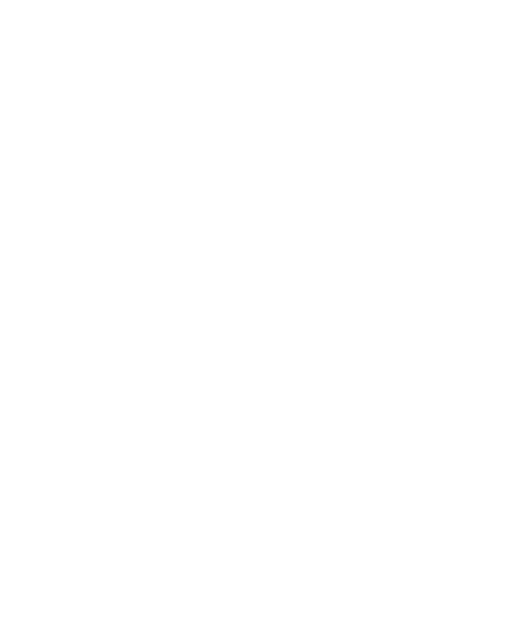程应峰
四十年前,刚恢复高考两三年。参加高考的人,年龄差距很大。大的三十多岁,小的十四五岁。相比三十多岁的,十四五岁就能考上大学的,自然倍受注目,总被冠以“少年大学生”之称而为人津津乐道。
一九七八年,我初中就要毕业了,同村有一位三十多岁的、小学都未毕业的年轻人,跟读在我们的课堂里,硬是凭着坚恝不拔的毅力,不耻下问,加班加点,刻苦钻研,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,向高考发起了冲击。天道酬勤,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,他总算考取了当地的一所中等师范学校。这,在当时也是百里挑一的了。
也有付出了不懈努力,却得不到回报的。我高中的同桌明子就是一例。他的父亲固执地认为,只要学业有成,作出再大的牺牲,都在所不惜。明子上高中时,父亲不仅不许他花时间做家务,也极力反对他与同学玩闹,说那些事都是在浪费光阴,会让他变得没出息。在父亲的调教下,他为学业付出了比同龄人更大的努力,将所有时间都放在了与学业有关的事情上。若是偶尔和同学玩耍、闲聊,就是父亲不责备,他自己也会觉得过意不去。就这样,他少言寡语,离群索居,一心向学。然而,怎么也意料不到的是,因长期缺少锻炼,导致在临近高考时身体不适,在高考考场上节节失利,终于没能挤过心仪已久的那座梦想之桥。
一九八0年,我参加高考的时候,也就是十五岁多点。那一年高考的前两个月,也不知是谁,到底和我有什么过节,或是出于什么心理,将我课桌中的书籍资料笔记本一夜之间盗洗一空,同年级全校有十多个班啊,每个班五十多人,唯独将我的偷了,也许是因为学校学习标兵栏里第一个是我的名字?也许是因为学校曾经让我佩戴着大红花在小镇长而曲折的古街道上,在全校师生的簇拥下走了一回?尽管受到如此重创,尽管心空蒙着一层厚厚的阴云在茫然中走过了这两个月,我还是在当年考上了一所大学,全校五百多名考生也就考取了七八个,能考取的就是凤毛麟角了。但是,那所大学与我的期望相去甚远,与头一年兄长考取的大学没法比。而家里太穷,无力让我复读再考。记得当时照毕业登记照时的4角钱,还是校长给我垫付的。
也就是这一年暑假,我呆在家里等待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,搬出了所有平时有心收集的过期杂志,逐一翻阅,把自己认为写得精彩的诗歌抄了厚厚一本,取名《诗海拾贝》,这一摘抄本成了我平生倾心于文字的一个拐点,一个开端。这些别有意味的文字,让我注意到了王蒙、纪宇、雁翼、刘再复……也让我从诗行中领略了文学世界的精彩和美丽。
上大学,尤其是上一所理想的大学,谁说不是青涩年华的一份至美的梦想?这份梦想,充满了人生前景的美妙诱惑。然而,并非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。一如俗语所说:“尺有所短,寸有所长”,“一个巴掌伸出去,五个指头有长短”,人与人是不可能整齐划一的,人与人之间总是存在命运落差的。说白了,凡俗烟火薰烤的尘世,命运这东西永远是难以揣测、难以捉摸的。
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年轻人高考落榜后的故事。他在高考落榜后,无所事事不说,还惯于争强斗狠。有一次,在一场群殴事件中,他将别人打伤,被判劳教两年。两年后,他从劳教所出来,母亲眼泪汪汪,父亲却若无其事,平静地对他说:“别在外面瞎混了,跟我打个帮手吧!”就这样,他跟着父亲当起了小木匠。一天,父亲让他将一根结满树痂的槐树木刨平。他虽然不明白父亲的用意,还是将它刨平了。当他把木头交给父亲时,父亲问:“你刨的时候发现它哪些部位最硬?”“结疤的地方。”他回答。“那你知道为什么吗?”父亲顿了顿,语重心长地说:“结疤的地方是它曾受伤的地方!每次受伤后,受伤的部位就会聚集更多的养分,长得更粗壮、更坚硬!你看周围的树,都是这样!”
事实上,人生的考试不止高考这一次,人的一生都置身于各种各样的考试中,有学业的,有职场的,有情感的,有伦理道德的,有人情世故的……无论考试的结果如何,都会让你收获一些什么。人生旅途上,每一场考试都值得回望。因为,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,都不会放弃自己的目标和追求,不会因为所走的路多一份曲折,多一份艰难而终日懊丧。夏日辉煌的太阳,明晃晃地照着,明晃晃地亮着,每一个努力付出、认真付出、执着付出的人,都可以在这份永无偏倚的明亮里,抵达充实丰盈的生命境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