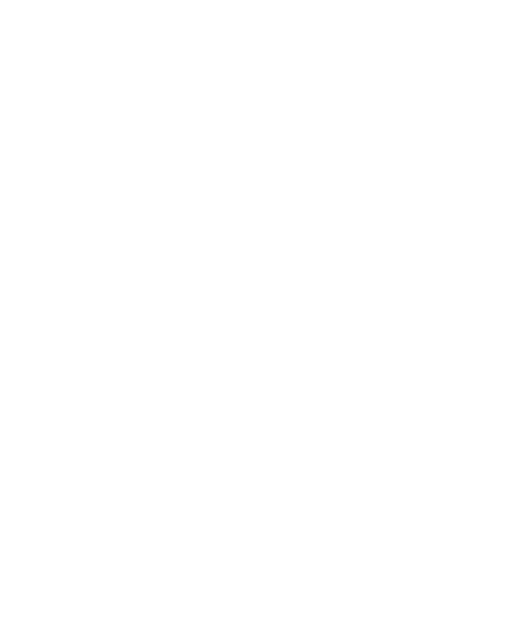覃儿健
好多年前读斯诺写的《西行漫记》,有个小情节觉得有趣。说是毛泽东主席喜欢在野外如厕。每当内急,主席便随手抓起一摞报纸,朝着警卫员嘴巴一歪,说:“走!”警卫员自然心神领会,也不多言,默默扛起一把锹头,跟在主席身后,屁颠屁颠往山岗上走。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,主席说:“好,就在这儿啦!”警卫员便在地上挖出一个土坑,找来两块石头架在坑边,这就成了主席的厕所。报纸看完了,肚子的问题也解决了。主席裤子一扎,铲几锹土将茅坑填上,屁股一拍,走人。
我之所以对这个事儿记忆犹新,是因为我也喜欢在野外如厕。记得小时候住在农村,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到自家茅坑里解大手的。每遇内急,我便抓起一本小人书往屋后山上跑。山上空气清新,又听不到大人的叫喊声,这时正是我翻看小人书的大好时机。伴着山林中鸟儿的鸣叫,我一边排便一边翻看我心爱的小人书,日子真是爽极了。记得那时我老挨母亲骂。母亲骂我“吃家饭屙野屎”。可骂归骂,每当我提起裤子往山上跑时,母亲却从不阻拦。我记得那时,几本小人书让我翻得像油渣片。什么《鸡毛信》《七天七夜》《上甘岭》《金沙江畔》……我不知看过多少遍,而且都是在屋后山坡树林间一边解手一边翻烂的。
我的这个习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。
参加工作后,开始当电影放映员,后来到县委办当秘书搞调研,再到后来当乡党委书记,只要是在乡下,只要一有机会,我都喜欢到野外如厕。而且每每这时,我都习惯拿一本书,或拿一本杂志,或拿一张报纸,边如厕边看。实在没有什么书可拿,哪怕是抓一张有字的纸片都行,似乎没有什么可读的就解不出手一样。
随着年龄的增长,随着环境的变化,下乡的机会逐渐少了,可如厕读书的习惯却根深蒂固。甚至觉得在厕所里读书有无穷的妙趣:第一,环境绝对安静。这时,妻子不会叫你洗碗,也不会叫你擦地板;孙子也不会缠着你讲作业。门门儿一关,整个天下都是你一个人的;第二,心是静的。既如厕来,什么功名利禄,什么恩怨烦恼,统统都不想了,天大的事情等上完厕所再说;第三,心情是愉悦的。如厕便是发泄。发泄总给人以快感,而快感能让人愉悦;第四,有时间。如得厕来,少说也要一二十分钟的时间。上了年纪如厕时间会更长一些。如想偷点清闲故意拖延点时间,在厕所里呆个二三十分钟那是常有的事。别看人生光阴几十年,大部分时间是帮别人做事,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不是很多的。给你利利索索三十分钟时间,能看很多页书哩!
如此者四,厕所倒成了我读书的好地方。我觉得在厕所里读书,人特别宁静,思想也特别集中,对文章的理解也特别透彻,一字字一句句,真的是入脑入心,过目不忘。
如此,好多书我都是在厕所里读完的。如《道德经》《论语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《墨子》《荀子》《韩非子》《吕氏春秋》这些儒家精典以及屈原的《离骚》《九歌》《天问》《九章》《久辩》等,都是我坐在马桶上一字一句啃读出来的。莫言的《生死疲劳》虽然晦涩难读,可冲着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名号,我反反复复读了三遍——近50万字的小说哇,足见我马桶上的坐功!
厕所里读书我是颇有心得的 。
晚清时湖南有个奇人叫杨度,他写过一副对联。叫做——
屋小堪容膝,楼闲好著书。
我得此启发,将此联略作改动,也得两句:
出恭堪作闲,入敬好读书。
出恭入敬都是上厕所的雅称。古时候科举考试设有“出恭入敬”牌,士子入厕须领此牌。意思是说,科举考场是个非常神圣的地方,士子上厕所出要恭,入要敬,后以出恭、入敬作为入厕的代名词。我的小文,便以后句为题。
满纸的臭白话,是为笑!